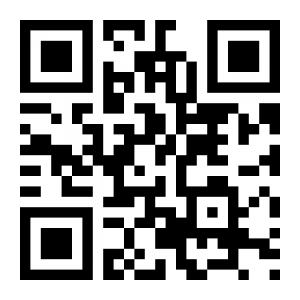只
林风眠早期作品的人道主义和后期作品中的诗意孤独,徐悲鸿作品对侠义精神、悲悯情怀和家国命运的深切关注,丰子恺的佛心与父爱,“决澜社”浪子们“狂飚一般的激情”,以至更晚的赵无极、李仲生对纯艺术、前卫艺术的追求,都折射着“五四”的启蒙精神。而蔡元培的“美育说”,鲁迅的“为人生而艺术”,宗白华的“境界说”以及滕固、邓以蜇、郑午昌、倪贻德、傅抱石、陈抱一的美术研究和评论,更以理性的成果表现着精英艺术在思想、情感方面的独立性和青春活力。
抗日战争爆发后就不同了。精神形而上的思索和个性情感的悲欢体验渐渐让位于“国家兴亡、匹夫有责”和“走出象牙之塔”的呼声。投笔从戎,宣传鼓动,文化下乡,中断画室书斋的创造,一切都服从于救亡之需。那么,“五四”精神还坚持不坚持呢?于是便引发了“文艺大众化”和民族形式问题的论争。一种意见认为,民族形式应成为文艺形式的正宗,而民间形式则为民族形式的“中心源泉”,并由此而推定“民间文艺为中国文学的正宗”。
另一种意见认为,救亡宣传不能丢掉反封建的启蒙任务,救亡文艺也应具有民主性的时代特征,因此,过分抬高民族形式和民间文艺,贬低甚至否定借鉴外来文化的观点背离了“五四”精神。在文艺与大众的关系上,前者强调“大众化”,后者强调“化大众”:即一个要求以精英艺术引导大众普及艺术,另一个要求以大众普及艺术改造或取代精英艺术。在重庆,两派观点采取了各行其是的态度。赵望云主编的《抗战画刊》提倡“绘画下乡”“绘画入伍”,黄苗子也著文倡导能让大众看明白的写实绘画,而批评“现代文人画”和西方现代式绘画与“大众的现实生活无关”。胡风、林风眠等则主张兼顾大众化与艺术的自身规律,不要为了一时的需求而丢掉纯艺术的、表达普遍人性、批判旧的国民性的探索。林风眠独居草屋,依旧醉心于他的“调和中西艺术”的实验。胡风在力排“民间文艺正宗”论的同时,对美术界由推崇战斗性而对雕塑、油画“样式本身也表示反感”态度提出批评。
在延安,也存在着类似的分歧,一些从大都市来的艺术家延续着20—30年代的传统,另一些艺术家则从宣传抗日的实际需要出发,提倡普及群众的喜闻乐见。1942年,毛泽东发表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》,一锤定音,肯定了“文化下乡”、“普及第一”、“喜闻乐见”,并把是否执行这一路线归结为“世界观”和“政治态度”。其结果是,在解放区出现了一批致力于大众化和抗战宣传的艺术家和作品,而把对外开放、个性解放、自由创造、独立精神性追求等“五四”精神驱逐得杳无踪影了。到50年代,全国统一,《讲话》被定为文艺的国策,持异议者如胡风被投入监牢,千万文艺家在欢庆国家统一安定的同时,也心甘情愿地改造思想,走延安文艺的路。于是,“年、连、宣”和各式民间工艺空前繁盛,雕、油、国诸形式日益通俗化、大众化,延安来的美术家成为美术界的各级首长,延安模式成为全国文艺的总模式。这种通俗大众化以政治目的为目的,以政治手段去推行,大多数艺术家乖乖地就范。
50—60年代培养的两代人,是吸吮着这种通俗大众化的奶汁长大的,他们对“五四”传统已不熟悉,他们甚至不知个性独立和自由创造为何物(或以为那都是“资产阶级自由化”、“裴多菲俱乐部”),他们终日所做的,“一是歌颂,二是忏悔”。在这样的情境里,除了个别艺术家的寂寞耕耘(如林风眠),哪里还会有精英艺术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