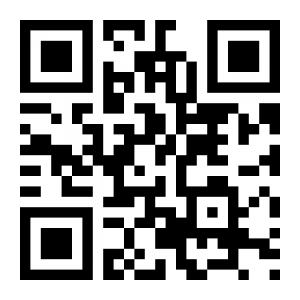姆谋
林鹏先生草书近作述评
发布人:网站管理员 发布时间:2015/1/4 点击次数:5138次
林鹏先生草书近作述评
——兼论衰年变法 刘刚
在书家中,我们常常会看到一种现象。早年或中年之时其作尚有可观,但进入晚年之后就会有两种趋向,其一是渐入佳境,越写越好,所谓“人书俱老”;另一种则是满纸习气,越写越俗,所谓“江郎才尽”,这后一种现象尤其严重,这现象背后的原因很复杂,它不是一般的“名利”或“学养”二事所能解释清的,这当中是否存在一个衰年变法的问题,所以很值得习书者深思。
目前看到林先生的一些草书近作,细细读来,令人精神为之一振,过后仍是回味无穷。同时对上面提出的现象也进行了一些粗浅的思考。下面看几件林先生的近作:
1、《读书一首》,六尺条幅,作于2012年,内容是林先生自己的诗作:“世纪风云吊诡多,图书万千一回穴。认真读去终觉浅,仔细想来不好说。读书一首。林鹏。”作品用笔气势盘旋,豪迈不羁,着实反映了作者放眼古今和读书后的思考。文中“吊诡”“回穴”之意,跃然纸上。
2、《自叙长卷》是林先生七十九岁时写给孙子的礼物,释文:我早年参加革命(抗日时期),是为了建立自由民主之新中国。3一九四九年革命成功,按年龄说,我应该去上学才对,谁知天有不测风云,该轮到我挨整了,这一整就是三十年(五十年代、六十年代、七十年代)。挨整三十年,读书三十年,这就到了八十年代。一九八零年,张颔先生赠我一副对联:“笔墨不求缙绅喜,声名勿得狗监知”,李炳璜先生对我说:“这是好话,你一定要接受”。从此名利之想淡而又淡,然而以仁为己任仍一日为泯。写了《丹崖书论》紧接着又写了《咸阳宫》,阐述“仁者无敌”之意。这就进入老年了。遂吟道:“天下大道多歧路,迷途知返时已暮,白首一言公无渡,公无渡,公无渡,枯鱼过河泣谁诉”二零零六年中秋节后孙驺虞完婚,吾非常高兴,漫笔诉此感慨之言云尔。林鹏于东花园诉此,时年七十又九矣。此作可以看做是林先生的《自叙帖》。卷长近二十米,笔法精湛,墨像丰富,因是自述,故感情饱满,气势逼人,堪称传世杰作。
3、《旧作俚句一首》,内容也是先生自己的诗文:天从人愿天作孽,民心向背民何求,出门静看东流水,不论成败以千秋。此作长六尺,用笔老辣,先天力可抗鼎。其独特之处在于章法,虽字字断,但其气韵贯满整纸,充分表现了一位士人为民呐喊的情怀。
4、《旧作俚句一首》,释文:春风春雨愁未消,绿水青山得逍遥。一路山花看不尽,倒骑毛驴过野桥。录旧作俚句一首,八五叟林鹏。作品长六尺,内容是林先生都市所感,其中不但有先生的历史观,同时也是他的艺术观。文句情景交映,寓理深刻,内涵丰富,整幅作品线条优美流畅,节奏上的快慢、顿挫、是笔法自然变化产生的效果。
当然我们还可以举出其他一些精品来,如:《蜀道难》长卷,《赠老妻》八尺条幅;一级那件著名的的长篇巨制《秋兴八首》等等,这里只是选出了具有代表性的四件作品。我们即可以做一个标本式的分析,在形似上虽然作品在尺幅上又大有小,条屏卷轴各不相同,但内容上都是先生自己的诗文。所以作品给人一种强烈的印象,就是任运自由,远观满纸云烟,大气磅礴;细察则笔墨纵横,变化莫测。总体风格气势相当稳定,而且耐人寻味。尤其在章法上开合自如,虚实相生。这充分证明了林先生八十以后的狂草艺术已经进入了新的境界,同时也可反映出其狂草艺术的独特风格。在这里我不惴浅陋,把这些风格特点,归纳出以下几点:
1、在笔法上,遒劲豪迈,八面出锋,点画不见起止,细笔有骨,粗笔含筋,线条刚进婀娜。
2、墨法上尤为讲究,因其用墨独特,真正达到了带燥方润,将浓遂枯的艺术效果。给人以生动自然地视觉享受,同时分寸把握甚为老道。
3、字法上以草参行,粗看满目云烟,不见字形,细读则字字遵循文字本身的天然形态。即便是相同的字也不故做人为变形。
4、尤其是章法上,一派天机,完全进入了无章法境界,古人有群鸿戏海,众鹤游天之喻,看上去绝无所谓的经营之迹。
5、在意境上,毫无装腔作势之意,因内容多为自己诗文,所以仿佛不是写给别人看的,完全听凭自己情绪的激荡,放笔直书,飘逸跌宕,妙若天成。
分析之后,我们是否可以从中得到一些启发呢?林先生在《丹崖书论》中反复提出他自己的艺术主张。如:“艺术的终极根源是在生活中。决定艺术家的思想气质的是他的生活条件和生活过程,而决定他的艺术风格的不是任何别的东西,正是他对生活的态度,是他的全部生活经历的升华”。我想,史上所谓的江郎才尽现象,不会是作者没有了生活,而是他缺少了一种将生活升华为艺术形式的能力吧!林先生一向以狂草名世,这与他丰富的阅历,坎坷的遭遇和率真的性情密不可分。他说:“没有法度而不得其门而入,死守法度则永远不能创新。所谓无法,也就是胸无成竹,没有成见,没有一定之规,没有什么一定的意图,信笔挥洒,一任感情的自然流露……如果在初级阶段只好降服在法度之内,而在高级阶段,正是要冲破法度的,如翱翔于高天,如方洋于大海。这就是孔子说的:‘从心所欲不逾矩。’这也就是傅山所说的用九。”我们看到这段论述后,回过头来再仔细读林先生的草书近作,我认为作于2005年的丈二匹十二条屏《秋兴八首》无疑是先生草书艺术的一件杰作,同时也是先生草书一书的一个转折。如果说在此之前是“有法以入”的阶段,那么之后创作的以上几件精品则明显已经走出了这一阶段而进入了“无法以入”的阶段。这就告诉了我们,在前一阶段,如果不进去,则终成所谓的外道。若出不了这一阶段,则又会成为傅山所谓的“里面的外人”,就会给人以“江郎才尽”之感。当然草书尤其是狂草创作之难,是有目共睹的,《草诀歌》开篇第一句就有“草圣最为难”之说。一位85岁的老人要在很短的一段时期内,创作出这么多的作品,不可能毫无瑕疵。林先生常说:“君子中庸,小人反中庸,君子中庸也,君子而时中。小人之反中庸也,小人而无忌惮也。”可见古贤之“中庸”思想,在林先生的艺术实践中是一以贯之的,是严肃认真的,人到老年要使自己的艺术得到升华,那绝不是一句写在纸上的空话,他需要丰富的能量储备。诸如人品、学识、个性一级人生际遇,精神上的涵养和实践等等。要想变法,复杂的很。林先生是研究傅山的知名专家,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:“傅山的这一创作原则(四宁四毋)是非常著名的,几乎是尽人皆知的,但是为什么后人不能像傅山一样付诸实践呢?不是后人不知道这样的原则,而是没有在反复临习的实践中真正理解它并掌握它。我们可以这样说,傅山自己也是到了晚年才真正将这一创作原则彻底的付诸实践,达到炉火纯青登峰造极的地步”。由此可见,一种艺术理论,即可成为你创作的源泉,也可成为你创作的陷阱,关键不在理论而在作者对理论的解悟能力。这种解悟实在说是一种政治上的觉悟和文化上的觉醒。它不是一种冥想,而是深深的扎根在实践中。诸如历史上的王羲之、颜真卿以及傅山等大师们无不如此。林先生在谈到笔法问题时曾说道:“笔法的关键是执笔法……彻底解决笔法问题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,而是一个实践问题,只有回到实践中去,长期的反复的临习和创作,笔法的问题才能真正彻底解决,等你解决以后,你也不知道怎么解决的,不要在理论上纠缠,不要在言辞上较真儿,那是没有实践能力的人们的事情”。此话明白晓畅,但也只可与过来人说。
几年前,林先生又写了本《东园公记》在一篇回忆挚友王朝瑞的文章中,有一段这样的话,很发人深省,抄在这里作为此文的结尾吧“说道进入老年,王朝瑞有一次问我,什么叫衰年变法?为什么要衰年变法?这是在一次笔会上,我们坐在一起闲聊时他说的。我说,这个问题太大,三言两语说不清,你现在已经进入老年,我告诉你说衰年必须变法,不然没前途。现在我也八十多岁了,至于什么叫衰年变法,它的内容,它的方法,它的目标,其实我也不知道。”我想纵如林先生这般擅长文笔的艺术大家,话也只能说到这里了,但林先生的实践以及他的思考实在是令晚辈敬仰,更值得热爱艺术的人们沉思。